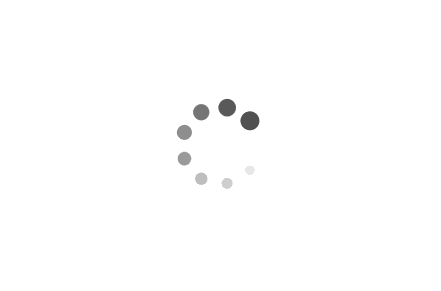覆鼎金考古遺址
| 歷史沿革 | 清嘉慶二十年(西元1815年)漢人郭百年擁眾入山燒殺劫掠,埔、眉番死傷慘重,抵抗不住漢人入侵的壓力,因此以水社番(卲族)為仲介,招致中部地區的平埔族群入墾,藉以對抗漢人。當時平原地區的平埔族群也因受了漢人的壓力,因此大舉率眾進入埔里盆地,從清道光三年(西元1823年)年起和安雅(Hoanya)、巴布拉(Babuza)、拍瀑拉(Papora)、巴宰海(Pazeh)、道卡斯(Taokas)等五族陸續遷入的有三十餘社,在「打里摺」的意識下完成結盟,並共同簽訂「公議同立合約字」來相互約束(劉枝萬 1954:39,洪麗完 2003),構成盆地內的主要居住民。在該次的大遷徙中,從豐原、神岡一帶移入埔里地區的巴宰族(Pazeh),則在烏牛欄台地上分別建立了大馬璘(今埔里愛蘭里)、烏牛欄(愛蘭里)、阿里史(鐵山里)三個聚落,稱為「烏牛欄三社」,因此愛蘭台地上目前居住的平埔族群聚落如烏牛欄、大馬璘、阿里史等大多是當時由今日台中市豐原、石岡、東勢、新社等地區遷移而來的巴宰海族(部份或稱噶哈巫族)。也由於平埔族大量由中部平原區域移住埔里,在逐漸成為優勢下,使埔、眉番因人口懸殊壓力,遂被平埔族群壓倒,或同化、或退入更偏遠的山區,至日治明治三十三年(西元1900年)年根據鳥居龍藏的調查,埔番只剩五人,眉番則近於消失,平埔族群人口便成為埔里地區的主流(陳俊傑 1997:20)。在清光緒元年(西元1875年)年清朝政府的理番政策運作之下,設立撫民理番同知,解除了漢人不得移住開墾埔里的禁令,從此漢人大量湧入埔里地區,使得平埔族人在人口上失去優勢,漢人文化成為埔里盆地新的優勢文化。 日治時期以軍事強勢統治,埔里成為以山區為主的能高郡行政中心,也是周遭族群如泰雅、布農等族社的物產與文化的交換中心,大埔城成為發達的街肆,不斷擴張,成為山區重要的城鎮。民國三十四年(西元1945年)國民政府來台後,由於228事件的抗議與示威,以及隨之而來的鎮壓與流血,至民國五十八年(西元1947年)3月4日反抗民眾在台中火車站附近干城營區組成「二七部隊」,後來改稱「台灣民主聯軍」,與國民政府軍隊對抗,由於顧及台中市民安全,二七部隊遂於3月12日退守埔里,3月16日小隊長黃金島在埔里烏牛欄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分別駐守烏牛欄溪南、北兩側的台地頂部小山巒迎擊國民政府軍隊,學生當場有四人死亡,最後彈盡援絕,黃金島等人雖極力突圍,退回埔里請求支援,但孤立無援,最後宣告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該次戰役稱為「烏牛欄之役」,3月17日國民政府軍隊在「二七部隊」解散後,隨即進入埔里,國民政府軍隊也利用了烏牛欄台地的軍事地理優勢,在埔里烏牛欄等地所在區域興建軍事營區(劉益昌等2009)。 本次調查研究所在的覆鼎金,就歷史時期以來的文獻紀錄,說明本地區曾經是埔社小聚落的所在,根據文獻爬梳研究,經過郭百年事件埔社引進西部平埔族群進入埔里盆地,迅速瓜分原有埔社所擁有的眉溪以南埔里盆地區域,埔社只殘存少量邊緣的土地。覆鼎金是當時埔社殘留的土地,根據清道光三年(西元1824年)北路理番同知鄧傳安到水沙連內山視察所寫的「水沙連紀程」,說明他到達埔里社的時候居住的地點就是覆鼎金山下的番寮,也就是埔社當時聚落的所在地(簡史朗 2002:37-39)。但是到日治時期初年,埔社後人望麒麟的居住地點已經在牛眠山附近而非覆鼎金,說明當時埔社已經不成為聚落也離開覆鼎金。 |
|---|---|
| 文化意義 | 一、考古遺址在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意義性: 本考古遺址由於可見繩紋陶文化層,具有可能早於大馬璘文化的繩紋陶文化內涵,且亦具有大馬璘文化層,也有歷史時期埔社的文化層,屬於多文化層遺址,但其文化內涵在埔里地區已有大馬璘、水蛙堀考古遺址為代表性遺址,不過本遺址所在位置有所獨立性,因此其史前文化意義當屬中級。倘若加上埔社在歷史時期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則本遺址的文化發展脈絡的意義則屬於高級。 二、考古遺址在學術研究史上之意義性: 本考古遺址為2002年簡史朗調查發現,並在2004年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調查紀錄之遺址(劉益昌等2004:0802-PLFTC-1),整體遺址之研究史略短,本考古遺址可能為原史時期以來存在但已亡失的埔社人群居住地,因此本遺址在學術史上意義,其意義當屬高級。 三、考古遺址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 本考古遺址文化層堆積在研究區域內仍可得見相當的文化遺物及文化層堆積,不過出土遺物或遺跡依本次試掘所見並不甚豐,不過具有大馬璘文化與繩紋陶文化之內涵,整體而言其出土之豐富度屬於中級。 四、同類型考古遺址數量之稀有性: 本考古遺址同類型遺址在南投縣及埔里盆地群區域之數量尚屬多數,如鄰近本考古遺址西北側的縣定考古遺址大馬璘、水蛙堀考古遺址,但出土罕見於台灣,且保存完整的喇叭型玉環,其意義屬中高級。 五、考古遺址保存狀況之完整性: 本考古遺址大部分區域由於早年開發及日治初年以來曾有公墓區,應有一定之干擾影響,不過由考古試掘所見仍可見史前文化層堆積,大部分區域保存狀況應仍相當好,不過由於考古遺址位於小丘,仍有坡度,易因雨水沖刷裸露,因此整體上遺址基本保存尚佳,意義屬於中高級。 六、考古遺址供展示教育規劃之適當性: 本考古遺址為一南港溪北岸的住居略顯分散的聚落範圍內小丘,鄰近民宅雖有但並不緊密,交通道路亦較屬縣道或產業道路規劃,相當適合於開闢成考古遺址公園提供展示教育規劃,意義屬於高級。 七、具其他考古遺址價值者: 本考古遺址文化層除具有大馬璘文化與繩紋陶文化內涵外,亦發現少量屬於與東部區域交換或交易之玉器、玉料,另亦可見玉器處理之切鋸刀,得以做為考古遺址交換體系形成過程研究之參考,在歷史時期相關事件以及原住民族埔社的存在位址,其意義屬於中高級。 八、遺址的文化資產意涵 (一)協助釐清大馬璘文化與繩紋紅陶文化的關係 透過本遺址的發掘,清楚得見大馬璘文化與更早階段的繩紋紅陶文化之間,是屬於上下層位的堆積,而且年代的差異相當清楚,這對於長久以來包括水蛙堀、大馬璘、坪仔頂等遺址尚未釐清的兩個文化層之間的關係,得到清楚的地層堆積相對關係。對於埔里盆地史前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埔番最後階段文化與根據地 本次調查研究確認清代末年以來埔社的所在地即為覆鼎金遺址所在的小山及其周緣區域,但從地層堆積所得的文化內涵,卻又說明此一歷史時期地層年代相當晚近,頂多只在19世紀後半。從清代初年以來的文獻紀錄,可以確定埔社的前身,或稱為蛤美蘭社(或稱蛤里爛、哈美蘭社)的聚落,應該不在覆鼎金遺址,而另有其他位置,根據劉枝萬先生說明可能位於今日枇杷城附近(劉枝萬1956:134)。這是未來必須透過考古學詳細調查的重要研究議題。 (三)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 從台灣整體大歷史的角度而言,類似埔番和眉番逐步消亡的例子,可說相當多,筆者曾經多次提出整體台灣的歷史必須涵蓋這些雖然已經消失,但是卻存在於他著記憶的人群,透過古文獻的解讀以及考古學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這些人群所留下來的歷史,曾經人數高達千人左右,領有埔里盆地大半土地的強大原住民族聚落,如今完全消失在歷史的洪流當中,但是人群遺留的歷史記憶卻完全表現在過去堆積的地層之中,透過考古學的研究,無疑可以讓這些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重新回到當代人的歷史書寫。 |
| 時代分期 | 新石器時代 |